目录
快速导航-
卷首语 | 卷首语
卷首语 | 卷首语
-

虚构空间 | 拿捏
虚构空间 | 拿捏
-

虚构空间 | 使北谣
虚构空间 | 使北谣
-

虚构空间 | 盐灯
虚构空间 | 盐灯
-

虚构空间 | 桑梓行
虚构空间 | 桑梓行
-

虚构空间 | 不要放弃
虚构空间 | 不要放弃
-
虚构空间 | 木盒
虚构空间 | 木盒
-
虚构空间 | 酸甜的西瓜
虚构空间 | 酸甜的西瓜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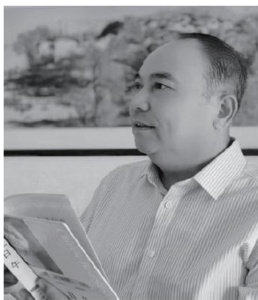
虚构空间 | 初恋
虚构空间 | 初恋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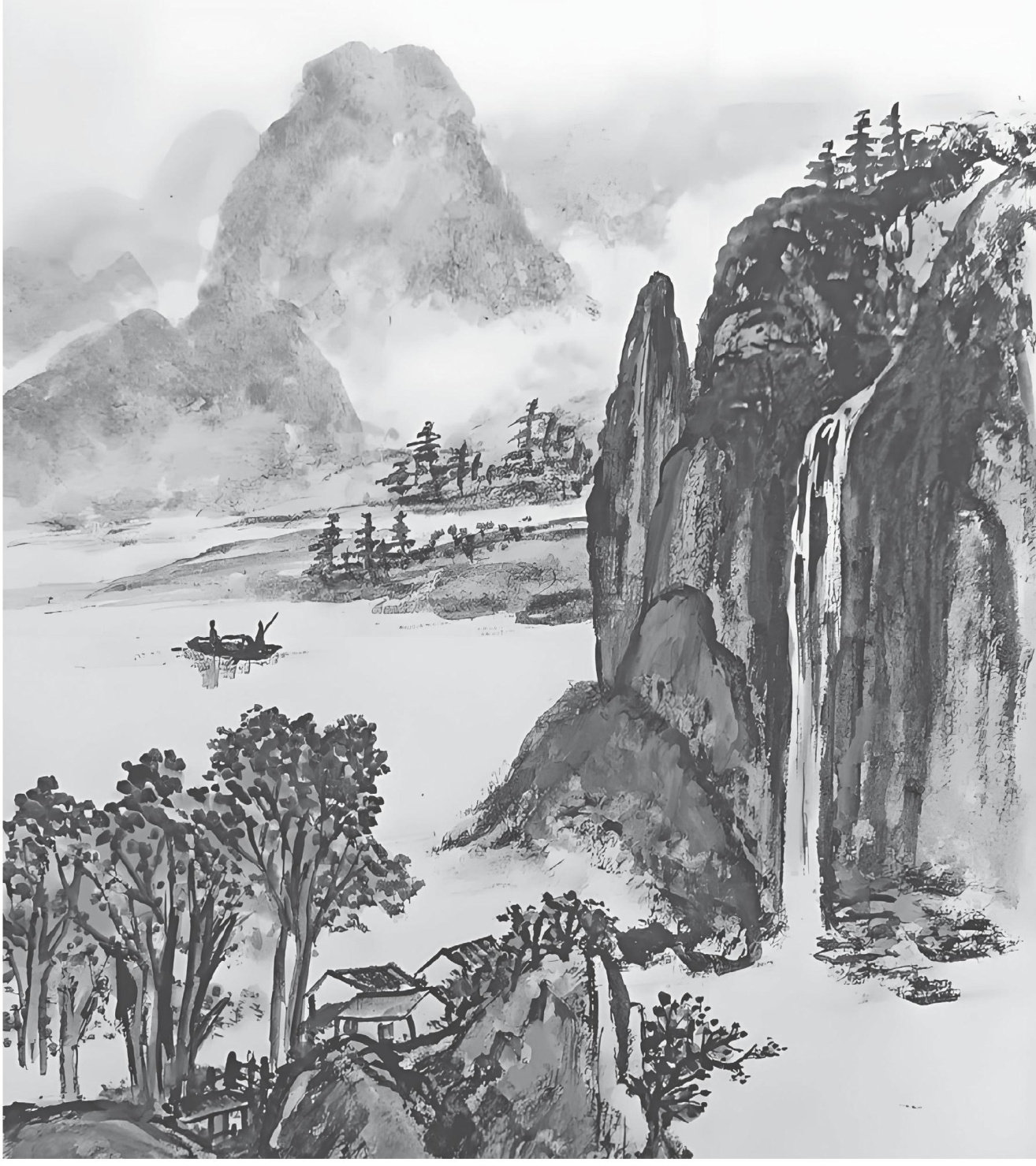
散文长廊 | 五十年感怀
散文长廊 | 五十年感怀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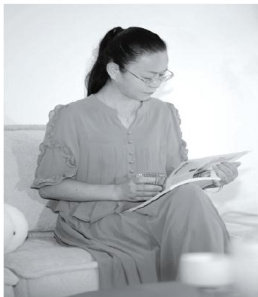
散文长廊 | 船娘
散文长廊 | 船娘
-

散文长廊 | 一路向南是南极
散文长廊 | 一路向南是南极
-

散文长廊 | 槐韵迢迢
散文长廊 | 槐韵迢迢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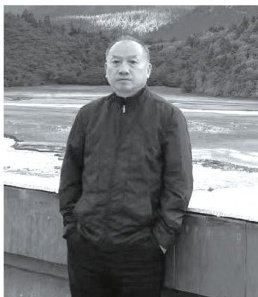
散文长廊 | 蝉鸣
散文长廊 | 蝉鸣
-

散文长廊 | 为母之路
散文长廊 | 为母之路
-
散文长廊 | 在时光的另一头
散文长廊 | 在时光的另一头
-

散文长廊 | 家人
散文长廊 | 家人
-
散文长廊 | 良师益友话人生
散文长廊 | 良师益友话人生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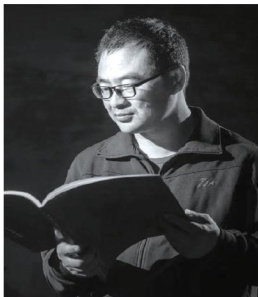
散文长廊 | 慈父手中针
散文长廊 | 慈父手中针
-

散文长廊 | 那一丛骄傲的菊花脑(外一篇)
散文长廊 | 那一丛骄傲的菊花脑(外一篇)
-

散文长廊 | 海边的日出
散文长廊 | 海边的日出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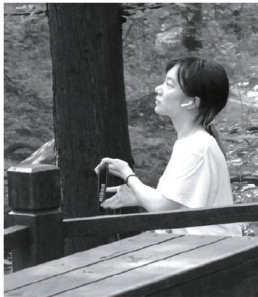
散文长廊 | 州桥夜泊
散文长廊 | 州桥夜泊
-
散文长廊 | 千年白果树
散文长廊 | 千年白果树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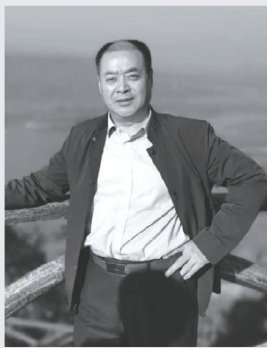
诗空间 | 蓝色的河
诗空间 | 蓝色的河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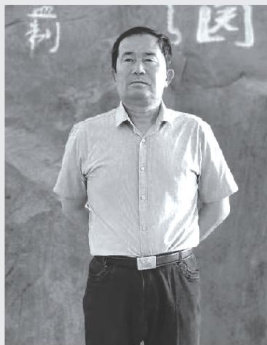
诗空间 | 谛听金水湾的蛙鸣(组诗)
诗空间 | 谛听金水湾的蛙鸣(组诗)
-

诗空间 | 始终朝着阳光生长(组诗)
诗空间 | 始终朝着阳光生长(组诗)
-
诗空间 | 诗空间
诗空间 | 诗空间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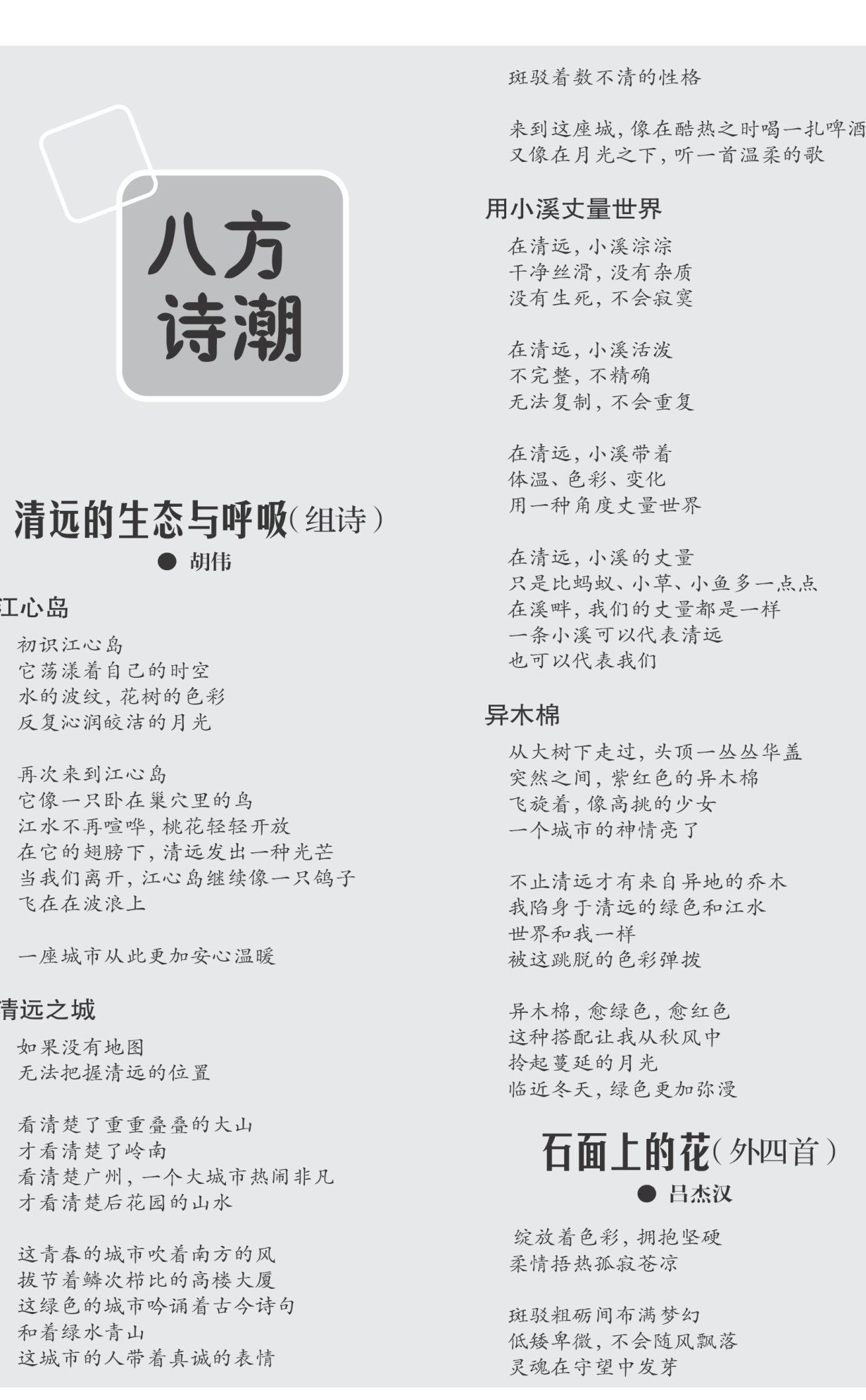
诗空间 | 八方 诗潮
诗空间 | 八方 诗潮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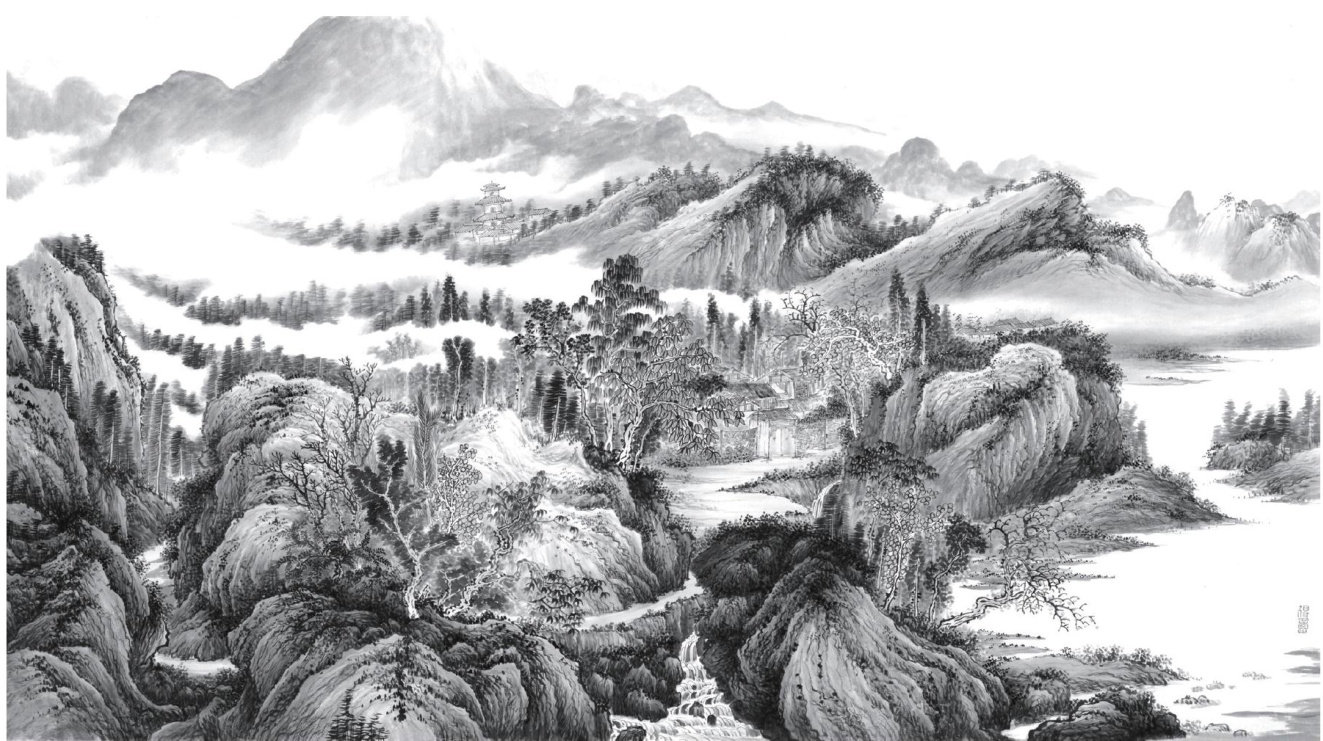
自由谈 | 历史人文的深情邂逅一 读范闽杰随笔集《遇见淮阳》
自由谈 | 历史人文的深情邂逅一 读范闽杰随笔集《遇见淮阳》
-
自由谈 | 时代审美的绿色重构与传统表达
自由谈 | 时代审美的绿色重构与传统表达
-
非虚构 | 奋楫扬帆正当时
非虚构 | 奋楫扬帆正当时
-
非虚构 | 陈家油坊根子红
非虚构 | 陈家油坊根子红
-
非虚构 | 追逐光,成为光,散发光
非虚构 | 追逐光,成为光,散发光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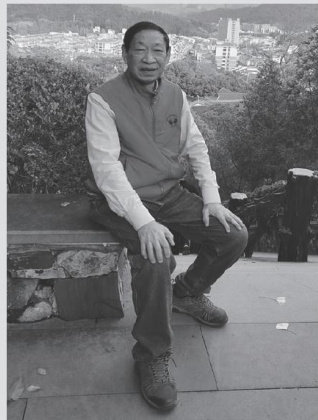
非虚构 | 狄氏春秋 连载(六)
非虚构 | 狄氏春秋 连载(六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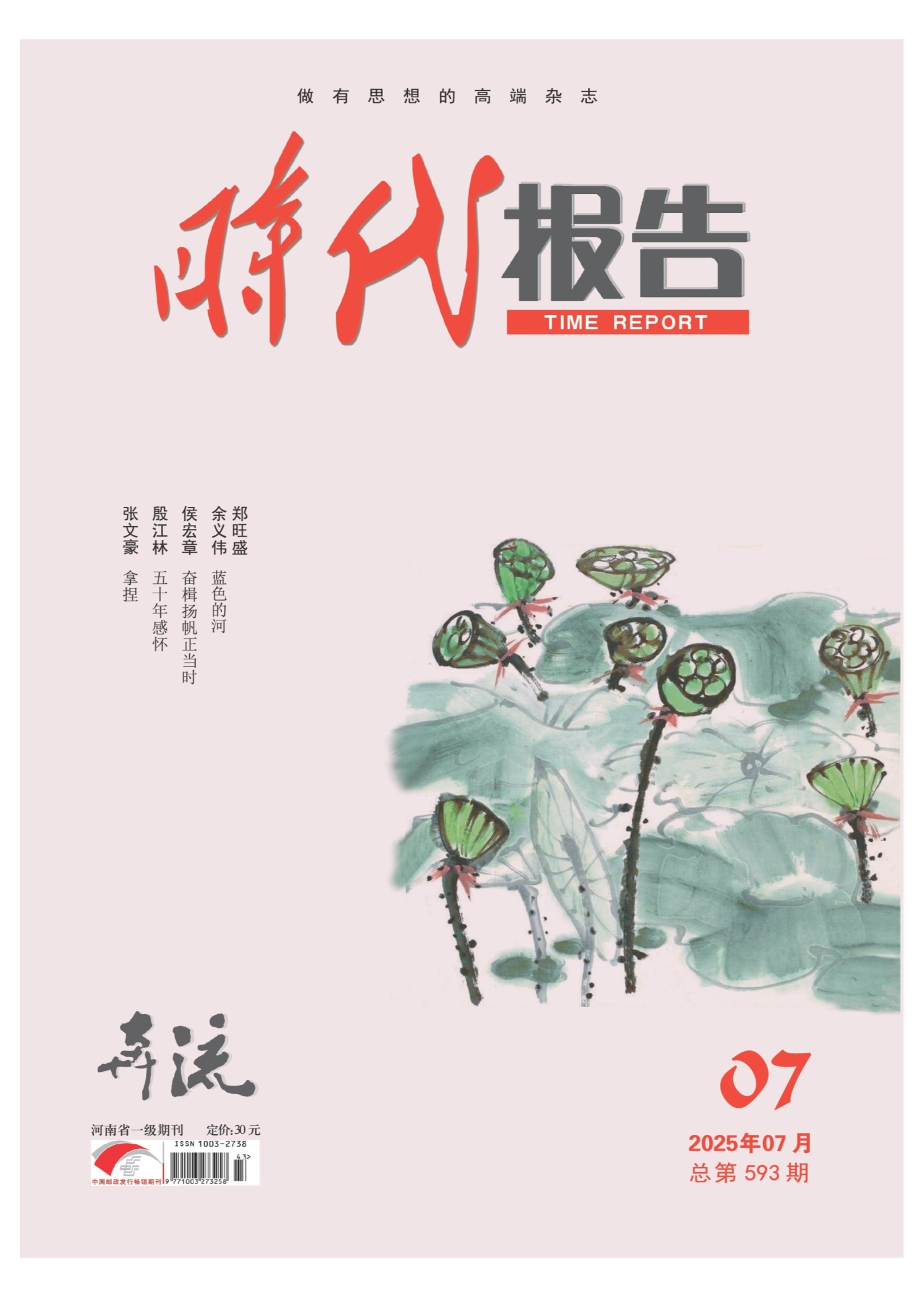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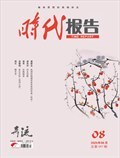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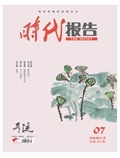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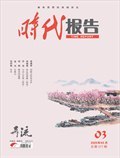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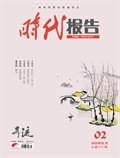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